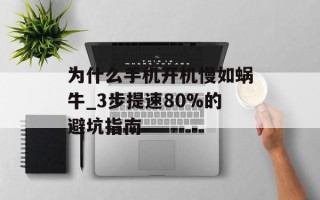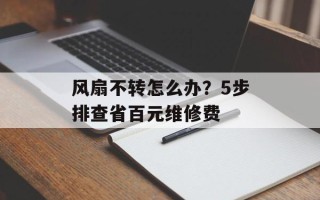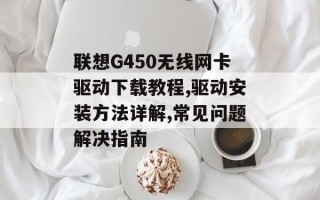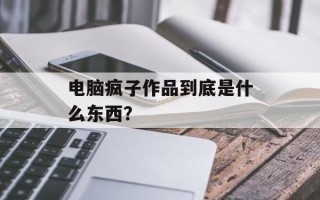很多朋友对于思想史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面和汪学群中国思想史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一、为什么要研究西方社会思想史
1、黑格尔(G.W.FriedrichHegel,1770-1831)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阐述了研究哲学史的理由:
2、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地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一如外在生活的技术、技巧与发明的积累,社会团结和政治生活的组织与习惯,乃是思想、发明、需要、困难、不幸、聪明、意志的成果,和过去历史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先驱者所创获的成果,所以同样在科学里,特别在哲学里,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这传统有如赫尔德所说,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3、黑格尔由此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哲学史并非外在于哲学的,“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2。
4、奥裔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在《经济分析史》之一卷的导论中则从教学的角度解释了研究思想史的必要性:
5、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3。
6、黑格尔和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具有一般的 *** 论意义,而非仅仅适用于哲学或经济学等特定学科,正如熊彼特所解释的那样,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 *** 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当前的问题和 *** 都是对以前的问题与 *** 作出的尝试性的反应。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 *** ,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 *** 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科学分析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持续的对话。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
7、与自然科学相比,学科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似更显重要。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明显的累积的和进步的性质,对一个学物理的学生来说,真正的科学典范是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而不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物理学”,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兴趣总是优先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并且很难以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对之进行处理,在这点上,社会思想的历史地位更似于哲学、艺术、文学与宗教等学科。差不多每一种现代的 *** 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把政治社会视为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这样一种真正的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仍对今天的功能 *** 具有启发意义;现代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L·V·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1901-1971)称赞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宇宙的系统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基本的系统问题至今尚未过时。”亚氏之被尊奉为现代系统理论的伟大先驱确有学理脉络上的根据。而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更从亚氏“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中,发掘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最早起源4。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有些人比别人得到的多一些,但完全得不到裨益的大概很少。“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5我们不能不读前辈思想家的著作,不能不吸纳巨人的气息。如果我们对社会学的遗产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恐怕很难有大的作为。我们的视野和思想深度必然受到限制;我们会犯本可以避免的或低级的错误;我们会忽视最吸引社会研究者注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是社会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问题;我们自以为是的新观点也许早已为前人所提出。中外许多学者早就认识到,“超过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6,这一洞见也是研究社会思想史的主要理由。

8、对于任何一门思想史,我们所能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它能向我们展示气象万千的人类思维 *** 。研究社会思想史可以训练社会学家学会理解、欣赏和公正评价与己不同的各种思维取径。过去的著作为我们保留了各种看问题的 *** 。前人依据这些 *** 看待各种社会事实,从而开阔了我们的历史视野和社会学视野。与过去时代的思潮的代表人物的对话,有助于培养多元开放的胸襟,发展理性的怀疑精神,戒除囿于一己的偏见。
9、一个易被忽视却相当重要的事实是,社会思想的题材自始便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就构成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境遇造成了多少不同的社会事实与问题,从而形成多少不同的社会分析的兴趣和思路,仅此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社会思想的历史。让我们对这一点稍加说明。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生活就是希腊人所能感受和想象的整个世界,故其社会学的视野也以城邦的城垣为界。希腊社会思想的主题关乎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基本单位的城邦共同体;关乎城邦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政治学)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伦理学),希腊社会学因此可恰当地被称为城邦社会学。在希腊化与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大帝国将城邦制度无情地逐入历史的后台,社会学的旨趣亦为之一变。世界公民的观念、人类的观念取代了城邦公民的观念,世界主义的理想取代了城邦主义的理想。进入中世纪,在世俗社会组织之外,出现了依共同的信仰组织起来的信念共同体——教会。在基督教思想家眼里,一切其他的社会组织或关系都失去了重要性,只有信念共同体才是最完美的团体;“拯救”被视为人生和社会最重要的事业。这样,中古思想较之古典思想又有一重要变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被人与上帝的关系的问题所代替;在时空中产生和消亡的东西,只有纳入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架构和短暂的尘世与永恒的来世的概念结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在近代两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和日趋技术化的社会,这样,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重新获得了世俗的和经验的性质而被置于社会分析的中心,但其题材和旨趣也与先前极为不同。工业社会是以国家(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经济的与社会的共同体)分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方面,“社会从前工业的、高度集权的系统向着分权的、复杂的工业系统发展,其特点是各种独立的组织的增长,它使不同社会集团和社群能够根据同其他人的关系确定和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扩大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7;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与科层制集权的加剧,导致了一种更有组织和更加集中的国家,这样,分权的市民社会与集权的国家的矛盾及调适的关系,就成为现代社会学关心的重点,从中发展出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交往、角色扮演、民主化、理性化、现代化、异化等概念和主题。而这种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主题却是希腊人所根本不知道的,因为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包含了生活共同体(自足的经济单位)、政治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在内的广涵的社会共同体。今天,西方社会是否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仍是一个争讼纷纭的问题,但以工业化、城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性是否如它承诺的那样将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地区战争、集中营、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后,是无法遏止人们的疑虑的。质疑有关现代性的道德主张、传统规范、中性程序和客观法则的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勃然而兴的8。今天,更有人要求以地球为参照点,发展一种可名之为“全球社会学”的视野,以全球性(globality)来取代现代性(modernity),有学者概括出能使我们超越现代性种种假设的五方面的原因: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性破坏性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信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显现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9。
10、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表明,只有把社会思想当作一种历史学的题材,注意其与时代兴趣、社会背景及当代生活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分析的旨趣、思路、特点及实质。西方社会经历了城邦制度、世界帝国、基督教信念团契制度、工业社会组织等发展过程,并且正在经历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最新的社会变迁,相应地就有城邦社会学、世界主义社会学、基督教会社会学、工业社会社会学及各式各样的“后学”。社会思想是关于社会过程的系统化的观念,是川流不息的社会生活的理论反映,但其本身也是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除非这些观念得到社会学的处理,否则,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会遗落于社会学分析的领域之外。“获取有关一个社会的社会认识的知识,意味着同时便获得关于那个社会本身的知识。”
二、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中观点对吗为什么
我来帮您回答吧,本人一向原创,不喜欢抄袭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句话说得比较有道理
看到LS有人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来说事
我曾经为这个回答过一位朋友的问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定义封建社会的问题
这里面我分析了马克思看待历史的主观性
马克思无法去观测所有的历史事件----更不可能去亲身经历那些历史事件,选取的材料,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的,都局限于欧洲---无法解释东方的政治经济发展
有关于您这个问题,我曾经回答过其他人类似的问题
“史书是人写的,难免主观,所以根本就没有真相。况且几经篡改,我们该信仰什么?”
下面是我当时的回答,完全原创,自己觉得写的还凑合,您可以参考
本人对哲学历史都比较有深入的思考,以下完全手打,希望您能够尊重
您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很欣慰现在有人能够做这样的思考,您真的很了不起
我只能在这里尝试性的讲讲---您也知道,说的太直接影响不好
历史的资料都是人来记录的----都是主观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真相
我们首先就要问一个基础,却又十分复杂的问题----什么叫真相?
这个问题可以写上100万字都不在话下,历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做过深入的探讨
大多数哲学家得出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认为真相是一种可证明的,符合逻辑思维的,真实的信念,知识或者想法
但问题在于历史学的记录很难符合这种表达方式
首先---历史的“真相”很难以被直接的证明---我们无法回到过去
而历史的“真相”也很难被模型化,来设计一个实验来判断---原因在于历史难以被数字化
更重要的在于历史书籍是人写的------而个人的主观思想会在文字上体现出来的
同一句话完全可以以不同的语气和语序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样,历史学本身就很难被称作是能够发现所谓真相的科学
于是,一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试图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 论统一----认为历史的记录与研究仅仅是在预估范围上误差更大而已---而且不具备重复实验的可能---而 *** 论上和自然科学一致
他们这样试图证明历史的记录通过历史学家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模糊的真相----相对自然科学来说误差更大一点而已
但是,问题在于----自然科学真的就存在所谓的真相?
您如果想到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本人写过专业论文)
首先,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于数学,模型 *** (建模)和测量
这三样东西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数学和模型是自然科学的表达方式----这意味着计算与公式的构建
而测量则是获得实际数据的 *** -----问题在于数据---和史书一样----是人测量出来的
哪怕是再精密的仪器----人为的因素仍然会产生不确定性
那么,如果不依靠人的测量----比如用光来丈量长度或者速度,会得到准确的真相吗?
海德堡测不准定律告诉我们----光也做不到,如果用光来获得更为精确的空间位置数据---则速度的数据的精确度会下降
如果用光来获得更为精确的度的数据---则空间位置数据的精确度会下降
所以,就连光都是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主观描述”的
可见,宇宙中并不存在永恒的真理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时刻在运动的世界
这好比,经济预测只能依仗原来的数据,总是存在资料滞后的问题
我们观测遥远的星系的时候----光线都需要时间来传播回来---我们不可能在一个event发生的同时---之一时刻就能获得关于其的一切
但是,不光数据的测量,历史的记录可以有主观
思维方式,模型的构建---也是主观的(这个论证起来很复杂,我写过一篇1万字的论文,有机会具体聊)
模型的构建不是纯粹的推理----而是一种跳跃式的,或者更直白的讲---就是一直巧合或者一个画家的绘画过程----很难有什么重复性,有着太多的偶然因素
例如原子模型,弦理论模型---很多并不是所谓科学的逻辑的产物
而科学家们却试图在这些模型被偶然的创作出来后
告诉大家----这些模型是通过一种合乎逻辑的 *** 来 *** 出来的
他们试图逆向推演模型的构建过程
仅仅是为了证明---我们和风水先生是不同的
而他们却在试图把科学变成一种新的神
该回答您最后的问题了-----我们究竟该信仰什么呢
我告诉您我的答案吧----您应该信仰“偶然”
偶然是宇宙间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频繁的东西
偶然性贯彻了这个宇宙,无外乎所处的时空和位移不同而导致的偶然性的大小不同
也正是一个偶然,能够让我有机会给您答题。。。
其实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学家当然不会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枉然
最后,我用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回答
历史学家研究了一辈子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古人的记载是正确的。。。
希望您能满意我的回答(估计不会完全满意的)
您这样善于思考的人不多了,希望能和您结交----别忘了加我好友
三、什么叫做“思想史”
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现在的思想史有很多写法,原来的思想史就是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史,每个时代的代表性观念就是通过这个时代的若干的大思想家的体系呈现出来的。后来因为每一代思想家都想做一点跟前人不一样的东西,于是就要找一种没有思想家的思想史,也是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史体现在大量民间的、非经典文献的材料中的,这样的思想史写法也是和哲学背景有关系,前一种传统的写法是特别黑格尔的,和黑格尔的整个历史观是完全一致的。黑格尔说历史就是时代观念外化的结果,所以每个时代就是在它的哲学里面找到自我意识,就是时代的观念反应在哲学家体系的概念里面。后面一种写法就像福柯的写法,譬如疯狂的历史啊、临床医学的历史啊、性的历史啊,这个就是偏到社会史上去了,这种思想史就渐渐偏为社会的观念史,思想史在英语里有两个对应的词,一个是the history of idea,就是观念之历史。一个是intellectual history,这个是对应于希腊的nous的翻译,就是心智mind,德文翻成精神之历史,这个精神就是指客观精神的历史,就是体现在制度习俗文化当中的观念。那么这个就不一定是思想体系了,但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个就反应在思想家的体系里边。这两种一种是学黑格尔的,完全掐断时代,把时代的一面不要了。还有一种就是把思想家体系的一面也不要了。写得极端了就成了没有思想家的思想史。这个路向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它和一个时代苦心积虑写出来的经典著作肯定是不能一视同仁的,否则最后思想家这种人就不需要存在了,这样的思想史的新的写法是对思想家、思想这种事业的否定。他觉得老百姓的日常言论里边存有思想,这个是当然的,因为它有观念在里边,可以挖掘出东西来,但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说得作为严肃事业的思想呢?显然不是经典就是这本书已经权威到够得上“经”了,严格的说老子庄子都不是经典,因为它过去是属于子部的,今天我们把重要的东西都叫做经典。在重视阅读经典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理想和教育理想是统一。任军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副教授):思想史这个概念是非常广的它直接和问题联系到一起。我们主张的思想史可能和一般所理解的思想史有区别,并不是历史学领域所谓的有狭义的思想史。譬如三农问题,这是属于我们研究思想史范畴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是要纳入历史学的研究分支里边去。只要关注一些我们有焦虑感的问题,对中国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敏感,而且涉及到观念层面,都属于思想史范畴。我受柯林武德的影响比较大,譬如美利坚立国,现代历史学科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它作为思想史事件就要求我们进入立国文献本身,探寻它在整个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位置,以及回应了一些什么问题。要放在政治思想史传统里去理解,当时的立国者是怎么想的,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一旦进入他们的脑海,就不仅是政治史的层面的一个事件(event)而是一种idea不然就只是罗列事件。林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问题关系非常密切。外在的说,哲学史主要是围绕它的学科的传承传统一脉。而思想史从范围上讲要大的太多,涉及到各种活生生的历史的社会的跨学科的领域。关注的问题上说,每个时代都有它关注的时代问题社会问题生活问题,所有关照都是基于这些问题的,但是把这些问题凝聚在哪个点上是各有不同的。哲学的研究是把这些问题凝结在一些核心概念,譬如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反思。而其他的学科,譬如科学家会用科学实验之类的方式表达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但思想史的焦点是比较多的,这个是他和哲学史的比较明显的差异。以康德为例,康德的影响和哲学史的地位是不用多说的,他是一个集大成者,甚至是一个立法者,谈到和中国的关系,牟宗三已经做过很多工作,譬如他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对知识论的态度。所以思想史并不是一段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从A到B的东西,有时候某种想本身就凝练了思想史。它自己有它自己的生命,会不断的自我生长出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从不同角度去观察那些即使是很遥远的思想,会发现它实际上仍然在影响你。当然这与观察者本身有关系。曾亦(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我现在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谈“思想史”的问题。社会思想是与社会学相对应的,它一开始就要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关系。从社会学这个现代学科看,它需要社会思想,但是,按照一般的见解,社会学是把社会思想看作是社会学的前史,也就是说,当科学还没产生之前,人们面对某些同样的问题的一些解决办法,这是前科学的,因而是朴素的、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办法――这就是社会学眼中所理解的社会思想。所以,现在一般搞社会学的人会认为思想的科学性不够,如果说有正确的地方也仅仅是因为它带有某种朴素科学色彩,如果它不正确就是因为它没有采用现代科学的 *** 。我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没有注意到思想,特别是作为一般思想所具有的特点。就是说,现代科学产生以后,思想还是继续存在的。科学首先标榜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但是思想不同,它跟现实很近。而且,真正能够影响现实、改变现实的不是科学而是思想。譬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刚刚传入中国之时,一批留英留美的学者回来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但是,这些科学研究并没有引出正确的结论。原因就在于,真正拉动中国现实发展的是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也自称是科学,但是,它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同,而是与空想相对的“科学”与现代运用经验 *** 的科学不一样。当时 *** 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但是, *** 由此获得的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与当时社会学家的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许会奇怪,那种严格科学研究为什么不能了解中国的现实,更不能预料到中国未来的发展,相反, *** 对于中国现实的了解,更近乎一种思想,它犹如一匹奔驰的马车,拉着中国现实奔向一个 *** 设想的时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在科学泛滥的时代是如何展现其价值的。那么,回到学科门类中的社会思想史来看,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一般思想史的特点,那种对现实的关怀才是其思想的正确性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较之简单从收集材料的经验科学,要密切得多,也更为真切得的了解到现实的实际情况。张巍(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简而言之,思想史就是用历史的 *** 来研究思想。这不是一种历史学科当中的思想史研究,因为它的目的可能不在于历史,而在于思想。历史系的老师可能会更关注历史,以历史为目的,以思想为研究对象来重构历史,这可能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而我虽然身居历史系,但是我比较强调的是思想,以思想为目的,用一种历史的 *** ,去研究并非代表、我们民族的思想,当然中国古代的东西可以做思想史的研究,但使我们这个中心可能更强调的是对西方思想的研究,所以对西方的所谓“异己的”思想的研究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我所说的“历史”是一个广义的包括文化的历史概念。譬如说研究的柏拉图,如果你仅仅是从他的《对话录》的中译本来做研究的话,那你几乎不避免的在做比附,因为首先之一层的翻译过程中有不少东西就是比附的,比如说他那著名的idea,以前翻成理念,现在很多学者说这个理念不对,陈康早就说要翻成相,还有学者说翻成形。如果你不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看到理念这个词,你就会按照汉语翻译去理解。当然重要的概念远远不止这一个。所以如果你仅仅依据中译本并完全忽视古希腊文化做研究的话,就没有思想史的层面,研究者可能认为直接在与柏拉图对话,可以把历史悬置,把古希腊文化都搁在一边,这样的研究肯定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所以我强调所谓的思想史研究,举个例子,你去研究柏拉图,就首先要恢复它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层面,只有如此你才能真正的理解柏拉图的精神,以后你在谈思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所以思想史研究是我们自己进入思想 *** 。我非常关注柏拉图哲学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对于柏拉图来说什么是philosophia。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哲学观念,把后世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强加到他头上的话往往会误解他,那么就必须到当时的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文化背景里去理解,等你理解了以后就会发现这个philosophia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我认为思想史的魅力之所在。或许思想史研究本身就需要找一个很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对象,这个可能不必思想史研究的 *** 本身更不重要。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副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更多人的更长时间的学术研究才能作出回答目前我只能泛泛的谈一些。现在有一种态度,就是把思想史当作资料或者思想史材料,就好像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出土文物,譬如发掘一个瓷器,去判断它的时代、用途或有此推及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这样的研究当然也可以当作思想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当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它本身并不就是思想史研究。实际上,当我们这代人对历史上的某个思想发生兴趣,是因为这个思想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实际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整个意义系统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思想史研究在我看来是一个追根溯源的工作,或者说是一个祭祖的活动。因为我们的意义系统、生活实践是从这个系统当中出来的,所以我们去研究它是要回到我们所来自的地方,重新让传统的起源在我们的生活中涌现出来,从而维持我们现在的意义系统。就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讲,这个传统可能主要是某个固定的传统,譬如儒家传统,当然儒家传统也是有很多源头的,只是后来融合之后似乎看起来是个源头。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它的源头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不仅仅是由整个传统发展出来的意义系统构建的而是来自于好几个源头。我们要回到它们那边去,要为了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意义能够获得一种理解。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史和思想史不太一样,哲学史讲究概念,尤其是黑格尔以后,强调概念之间的关系,要讲清楚每个时代凝结成的概念之间的逻辑。他提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重在把逻辑关系讲清楚,这在某种意义上把历史给涵盖掉了,因为历史的变化是通过不同的哲学家体现出来的,哲学史就是要讲清楚这个。然而哲学史的工作又很多缺陷,它更注重哲学内容的发展理路和逻辑关系,它把哲学家周边的生活世界、历史背景和整个问题产生的外在语境的重要性降低了。通过思想史可以再现概念产生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像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就是一种典型的把哲学还原到思想史的研究。因为研究明宋理学,你也可以讨论理、士、道这些明宋理学里边的概念,但是余英时把谈论这些概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意涵了什么东西,这就让整个干硬的哲学概念还原到活生生的历史环境里去了。这就是思想史对于哲学史的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哲学史又有它的意义所在,譬如说洛克,有的研究者就说在洛克身上有五大神话,譬如把他看作自由主义的鼻祖,看作光荣革命的理论阐释者,看作辉格党的理论代言人等等,但通过思想史的研究可能会揭穿这些神话,发现某人不是创始人,或者不是某种理论的代言人等等。但是对哲学史来讲,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重要。它关注的是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的思想,而不在乎它究竟属于哪一个人。这一点来说,哲学史对思想史也有一定的补救作用。因为思想史毕竟是一个历史,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世界里边去,这样就可能会被很多细节吞噬以致于迷失,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既能把握主线又能展现那个丰富的生活世界和历史背景,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而不要执其一端,要么展现丰富性,消解掉它的意义本身;要么只讲概念,抹杀了它的活生生的来源。《思想史研究》之一期里面主要介绍了两个学派:剑桥学派和斯特劳斯学派。剑桥学派有一点毛病就是有时候过于注重细节,而斯特劳斯的研究个性更强,它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解读思想史的方式 *** ,譬如认为哲学家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显白的层面和一个隐微的层面。他用一种比较特殊的 *** ,经常能把思想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但极其有意义的东西挖掘出来,但我不觉得这个 *** 能够推而广之,在某些历史时段它是很有效的,但这个理论也有它的效用性和边界。
关于思想史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面和汪学群中国思想史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